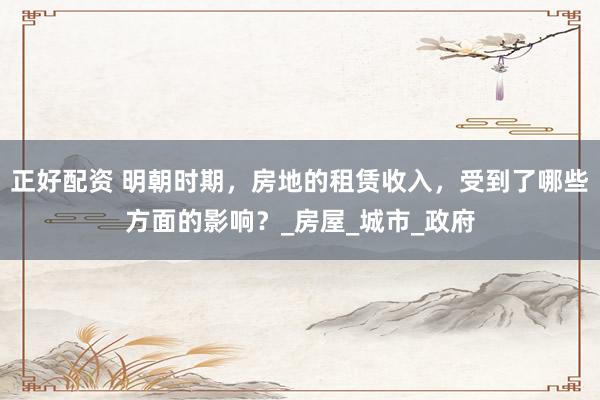
引言正好配资
明朝时期,房地的租赁收入,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影响?“房屋租钱”同时包含了房屋的税与租,也包含了房和地的税与租,故难以区分各项的具体收入。
明人在《姑苏志》卷15“房地赁钱”中记“元官房地粮六十四石,钞三百二十锭有奇”,可知其中有租赁收入,所征有粮与钞。
元代的国家财政收入中含有房地租,在元代地方志中多名为“房屋租钱”“官地租钱”“房地租钱”等。
虽然其具体租赁收入数额不详,但有“租”或“赁”的表述,即说明租赁的经济收益已包含在其中。为说明城市房地的租赁收入,仍然只能将录事司的相关记录作为主要参考。
如上引《金陵新志》中在城录事司(系官)税粮条下记“房钱二百六十五定一十九两三分一厘,内有丰和棚租钱一十二定”。
展开剩余93%其中,丰和棚租钱虽然数额不高,但明确是房屋租赁的收入。又如延祐《四明志》记庆元录事司有“官地租钱五锭一十两八钱五分,房屋租钱一锭四十八两六钱六分”。
这条资料中的房地租赁收入额虽然不详,但列于录事司之下,应是国家财政收入中取自城市的部分。“房屋租钱”“官地租钱”“房地租钱”等收入有具体记载。
说明元代将官产房屋、地基作为经营对象的做法延续了前代,并未中断。总之,据官方文献和所存方志,元朝房屋租赁和屋税收入一样,难以区分属于城市还是乡村。
不过,录事司的房地经济收益仍然使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部分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
一、城市房屋的经济收益
明朝继承了元代对房屋资源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利用,但较元代又有变化。明王朝建立后,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城郭、房屋等城市建设较前代突出。
各地依靠政府资金大规模修葺城池,且用砖砌,大大加强了防御的强度,城市房屋建设中官产屋舍的建筑尤为明显,其资金也多源于政府。
这些都为政府利用房屋资源获取财富提供了条件。明初以来,官府从房屋租赁中获取经济收入,而文献记载尤其体现出政府对官房地产的规范管理。
如对租钱的划定依据、交纳的数额、缴纳的时间、管理和使用等方面都有一定规制。但政府对房屋的征税比较杂乱,难以划定城市屋税,也难以确定是税还是役,等等。
大约至明中叶后对房屋的征税才逐步制度化:一是再次明确在城市范围内,二是确定房屋征税以间架计或以间数计,计税依据客观易行。
官产房屋租赁和对民间私房征税不仅是国家获取城市经济资源的一种方式,其收入同时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
不仅服务于地方财政,也在明后期为国家筹措军饷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城市建房为政府获取房地经济收益提供了前提条件。
自古以来,城市房屋建造的规模与速度就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观测点。
受元末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初创的明王朝着眼政权稳定,亟需解决一系列问题,如政权中枢能否正常运转,官员、军队能否尽其职守,百姓日常生活能否稳定,官民有无居所等。
从洪武中期至永乐年,朝廷在京城及地方动员官民兴建房屋,而官府是兴建屋舍的主力。
为稳定军队和官员,洪武十四年(1381),命“京卫营建军伍庐舍及官员居室”,十八年,令增建“京官居舍,造房舍凡百余所”。
二十四年,便有“京师辐辏,军民居室皆官所给,连廊栉比正好配资,无复隙地”的记载。
为保证行政效率,规定官员必须在官房内居住,“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内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
为发展文化教育,朝廷对教育机构(如南京国子监)的师生提供并修缮屋舍,“修完诸生亦各居号矣”。官府对寺院也予以支持。
《金陵梵刹志》多次提到南京报恩寺得到“拨赐官廊房”“钦赐官廊房”等优抚。
可以说,自洪武中期始,政府所提供的可居住的房屋,一定程度支撑了国家的正常运转和文化事业的起步。
为发展经济、鼓励商人和百姓的活动,政府出资在京城和一些府州县城营建房屋、店铺等,供百姓居住或方便商人囤货、经营,并按一定时间和房屋等级征收一定的租钱。
据《宛署杂记》载,明成祖为迁都北京改建都城,官府奉旨在“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
宛平县“共盖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云”。
此外,朝廷明令“准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并在崇文门一带“建设暂憩店房二百余间”,以便商人守候并办理查验手续时,可免“百货露积,致罹风雨浥损,盗贼窃取”之患。
除置官店塌房外,南京若“有房屋倒塌,止存空地若干,各该衙门另行盖造,以足官舍,以别民居”。
这些都是两京置官房以解决官府和百姓需要的记录,而在两京以外的其他城市也有建盖房屋的记录,如永乐十一年(1413)福建道等地官府即有盖房事宜。
为适应城市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政府鼓励百姓自建屋舍。洪武二十三年,有诏创制南京龙江、仪凤、钟阜三门。
对其周边民房“民能自造者,官给市木,钞每间二十锭”,以补贴民间建房资金不足。政府督促民房兴建是保护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
在政府积极倡导、官民共建的基础上,明两京及其他城市建筑发展迅速,两京及商贾辐辏之地多有房屋鳞次栉比的记录。
城市房屋建设不仅满足城市日益增多的人口居住需求,也为政府日后对房产征税和收取租钱提供了条件。
明代政府对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建城池、盖房屋)对后世的影响是前朝不能比拟的。
二、房屋的管理及租赁
明代城市房屋分官产和私产。官房租赁的发展更为明显,并形成了一定规制,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支持了国家财政,私房租赁的条约规范。
房主租客责权清楚,也可作为考察城市经济发展的窗口之一。官房的管理与租赁。
从前引建房资料看,官府所建房屋有“廊房”、“官舍”、“官店”、“店房”、“铺房”、“塌房”和“官店塌房”等称谓。
这里的廊房,与四周带有厅堂的一般建筑物不同,是官府为商人方便办理相关手续以及保障其物资安全而建造的屋舍,归官府管理,所以常常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出现于文献中。
明初两京的官舍、官店颇多正好配资,除去用于赏赐、官府机构和军队使用、官员及其家属使用的免租房外,其他房产多以租赁形式经营,但会因时代而变化。
根据前引史料,我们知道明代两京官房甚多,仅从《南京督查院志》卷35来看,就有政府对官产房屋数量、归属(御赐、免租等)及现状进行细致清理并明确造册登记的记载。
具体来看,洪武时期,即由工部对官房进行了编号和登记。据记载,为方便官员办公,官府欲在衙门附近起盖房屋,但是“今照各官房屋混杂居住,多有不便。
今后,着工部取勘各衙门官若干,该住房屋若干,编成字号。如或事故,新代替官员就住,仍将本房原有什物置立牌面,刊写相沿交割,如有损缺,就令陪〔赔〕偿。
今后合将官员见住房屋,各照原编字号造定文册,内府收照。官有事故,锦衣卫、兵马司同本衙门官眼同封记,候除官拨住,不许别衙门官员搀占居住搅扰,此编号之始”。
永乐年间,“太平门内两廊(笔者注:是官属所居之处)、东城兵马指挥司编号附籍。凡交代而居者俱转号以凭稽考。”
由此看出,早在洪武、永乐间,有司就对房屋进行编号管理,其中供皇上恩赐、官员、军队、官署等无偿使用的部分,应与租赁等经济收益无关。
随着私有化和商品化趋势加剧,明中期时已可以明显看到“系官房产”所有权混乱的现象,亟需加强管理。
嘉靖时就有官员认为,南京的“祖宗恩赐”房产已经“被军民之家占为己业,法司各官反行赁住典借,使恩制不及于品官,而官房混占为市业,若不清查,久愈泯没”。
因而呼吁“清查改正,一新旧规”。为此,官府再次清理房产,并规定了整顿规则:要见前房系何年月日各人居住,有无是何衙门出佃与人,或令看守修理遂相传业。
有无契券给帖执照及办纳何项租课,中间有无军民本等祖业相杂,各官见住者有无出银赁典或是借住,一一务查明白,取各亲供,备造文册。
该规定在南京东城、北城率先实行,主要由城下某铺总甲具体执行,如“北城廊下总甲李祚等,各开报前项房屋、地基、间数,并房主、赁住人等姓名”。
而后交南京司礼监进一步核查,“逐一查照号数,丈量明白”,等等。据北城兵马司清查房屋资料记载,其“计开”下西廊和东廊的房屋排号均曰“北字”号。
每间一号,排号至一千七百余,皆是官房号。从北字号居住者的身份来看,他们的社会地位不甚高,多为军人、锦衣卫、太医院、孝陵卫等人群。
从所登记某号房为何人居住的信息中,可见有一人对应多房号的情况,如西廊“北字七百一十四号、七百一十五号,锦衣卫于富住”。
“北字七百四十二号、七百四十三号、七百四十四号、七百四十五号、七百四十六号、七百四十七、七百四十八号,孝陵卫妇白氏住”。
以及“北字七百八十四号、七百八十五号、七百八十六号、七百八十七号、七百八十八号,太医院郑铭住”,等等。
同在“计开”的“西廊”“东廊”之下,“嘉靖十八年三月”间,出现有买民房充作官房的记录。
如东廊“北字一千六百三号,一千六百四号,留守左卫胥继祖住,嘉靖十八年三月买,今张字号官房”,等等。
又如,“张字号,坐御赐廊大直街,西向,嘉靖十八年三月买胥继祖房,精微簿北字一千六百三号、一千六百四号。”两京官房的租赁经营自明初就产生了收益。
永乐年间,官府在北京崇文门一带为商旅建有二百余店房,遂“仿市廛征商之法,量纳房租,共计一万二千余两”,起到“下不病商,上藉裕国”的作用。
又,宛平县建有“廊房八百一间半,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间半,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
官府将居住房“视冲僻分为三等:内大房四百四十三间,每间每季纳钞四十五贯,钱九十文,中房二十九间,每间每季纳钞三十一贯,钱六十二文,小房三百二十九间半。
每间每季纳钞三十贯,钱六十文。每季共钞三万七百一十八贯,铜钱六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文”。
而“店房一十六间半,每间每季纳钞六十贯,钱一百二十文。每季共钞九百九十贯,钱一千九百八十文”。
为管理租赁事务,“每季轮委佐领官一员,总领其事”,选廊坊内民有实力者为廊头。
“计应纳钱钞,敛银收买本色,径解内府天财库交纳,以备宴赏支用”。南京的官房租赁并获取收益亦早已有之。
三、房租银的记载
洪武年间,官府“拨赐官廊房四十二间”给南京大报恩寺,可“与常住讨房钱用”。永乐十年时,廊房因扩建寺殿而拆除。
至宣德三年(1428),官府再“拨廊房四十二间,“‘南’字三百十六号,至三百五十七号,四十一间,‘南’字七百八十五号一间。每间一年房租银三两六钱”。
虽然洪武间廊房的具体收益不详,但宣德年间对每年每间的“房租银”记载非常清楚。
嘉靖间,对北城官房清理时,要求“各开报前项房屋、地基、间数,并房主、赁住人等姓名”等,“房主”“赁住人”从一个角度说明官房租赁契约关系实际存在。
官府规定按廊房例,“每间量征钞贯入官”。万历三十四年(1606),报恩寺租户娄楩状告寺僧勒索钱钞,僧录司查明后,定房租“每间月征银一钱二分”。
明确租户不得拖欠,否则逐出不得居住。据嘉靖间对南京官房清查统计显示。
“今典卖赁借与各官房屋并空房空地共七十一所,计二百七十九号,内官家人住房三所,共一十七号,并军民高铠、曹通等自住房屋共一百四十七所,计二百一十八号。”
这些应是先前官府提供给官民军人等免租居住的官房,后来出现将官产私有化和非法经营的案例,官府分别给予不同的处理。
如将房屋典卖赁借,属于私有化经营,其收入为不法赃款,故“量员多寡,分属三衙门,各责首领官管领,查照各主原用价银数目,南京刑部、都察院俱于各赃罚纸价银内动支。
南京大理寺于南京工部匠价银内动支,俱各量给一半,以赎归官”。对多占的房屋,官府提出“合照南京廊房事例,每间量征钞贯入官,户部收纳以充公用,俾各照旧管业,以安生理”。
两京以外的城市官房租赁也十分普遍,其经济收益对地方财政十分重要。
洪武十年,杭州府仁和县“房地赁钱财赋赁钱四十六万五千三百四文,系官赁钱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七十文,没官赁钱五十一万八千二百一十四文”。
永乐十年,“没官房地赁钞五百二十八锭五百三十文”。成化八年(1472),吴江县“官房一万六千三十五间,岁办赁钞七百三十五锭二贯八百七十三文”。
弘治时期,福建福清县“官房屋赁钞,四百一贯二十文”。正德十六年(1521),大宁都司安乐置“新旧房舍数千间,有仁字店及南关厢米粟等房,听民间赁居,岁入租以备公费者也”。
嘉靖时期,赣州府有“官房赁钞,三十四锭四贯三百二十二文”。
万历年间的绍兴府有几个县记有租赁收入:“山阴官房赁钞一千八十四贯,诸暨房屋赁钱三百八十三贯三百三十文,上虞官瓦房赁钞二百四十八贯二百七十五文,余县皆缺。”
结语
苏州的资料有些特殊正好配资,史载:“洪武初,房地赁钱三百三十六万三千九百文有奇。弘治间,该钞五千五百九十七锭有奇。嘉靖间,止征长、吴二县,钞二千七百三十锭有奇,折银四十两有奇。”这里未注明“系官”或“官房”的收入等,但官房租赁应在其中。
发布于:天津市富灯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